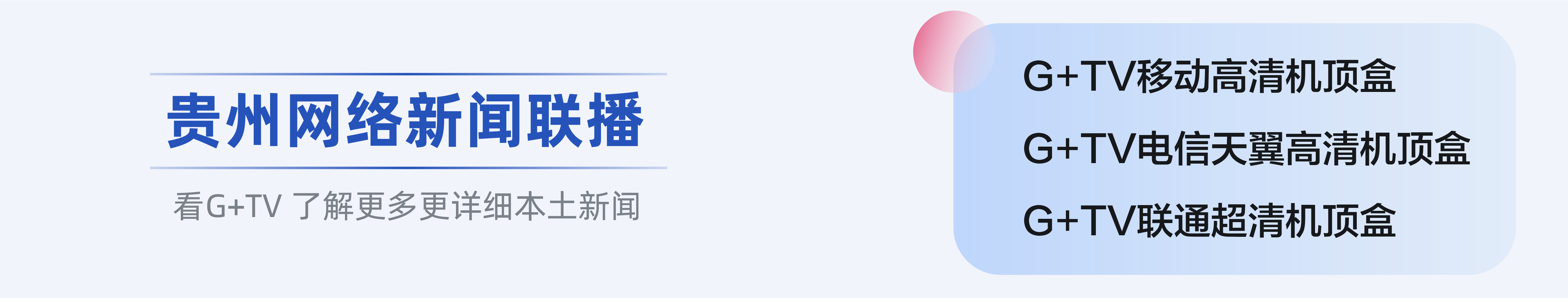先扯点闲篇讲一个多年前的冷笑话。2007年底,我闺蜜周哥劝我说,你还是应该学点理财的技能,于是他带我去证券市场花了一万块钱开设了股票账户,并指定我买了一只股票,那些K线图我是看不懂的,在我眼里,我觉得它就像一段音乐旋律的发展路线,忽高忽低,还挺有节奏,走一步探两步,又或者走两步探一步。周哥说,你不用看懂,每天回家后打开电脑,只要看见你的股票颜色是红的,就说明你的股票是挣钱的。那之后半年多的时间吧,我那只股票每次打开都是红色的,我默默在心里盘算,哦,今天又赚了一把白菜钱,股本少嘛,赚得就少,心里美滋滋儿的。周哥说,你不要急捞捞的天天看,扔那儿不管,过段时间再看。
有一天,我打开电脑的股市页面,立即致电周哥:“周哥啊,你来我家看看我的电脑嘛,是不是电脑显示屏出问题了,怎么股票颜色全部变成绿色了?”周哥听后气急败坏、勃然大怒:“猪啊!涨红跌绿,那是股票全部跌啦!”猪,没敢说话。后来,在周哥的直接操作下,没几天就把我那只股票卖掉了,保本。再后来,我那个股票账户早就被我遗忘,想不起来了。赚钱是需要本事的,靠投机不得行,所谓本事,既要有本金,还要有知识储备以及能力储备,猪如我,就算了吧。
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导致美国股市暴跌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当我学习熔断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的思维理解不在经济学的层面,而在音乐学的层面上,有时候,我们发展音乐表达情绪的时候,通常会启用休止停顿,以沉默来孕育积聚力量,为更加深刻的、激进的情绪做准备,以推动整首乐曲的音乐情绪到达高潮。
背离经济学层面的熔断机制概念,我想起一个人来,定居在湖北武汉的张武宜,他还有一个中国广播业界更为人知的名字:张弛。
 张弛:原楚天音乐台主持人
张弛:原楚天音乐台主持人
记住一座城,其实是记住一个人。我对武汉,或者说对湖北的记忆分为几段。很小的时候,我的记忆是武汉长江大桥,因为我爸爸有一张年轻时身着列宁式翻领棉大衣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黑白照片。到我读高中的时候,我的记忆是每个月我们家都会收到一封来自湖北孝感某部队的来信,那是我哥哥服役的空军某地勤部队。而后,我的记忆便是张武宜,我叫他五姨妈,他叫我莫孃孃,我们同龄且属同一个星座,五月的金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张武宜,哦,不,张弛是楚天音乐台的节目主持人,主持一档节目叫《关不掉的收音机》。一档好的节目名称是有生命的,并不仅仅是符号,仅就节目名称而言,它所蕴涵的表情、律动、节奏都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音乐广播节目里为数不多的节目名称之一。那个年代,动态的汽车、静态的汽车侵蚀了城市的交通、道路、图书馆、歌剧院,却复活了广播。那时候的广播主持人,尤其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的门槛好低,只要会说话,每天带几张唱片、带几本类似罗兰小语的书就敢进直播间,他们不兴写稿子的,乱象丛生,当然,淘汰率也很高,留不下几个好的。而张弛和他的《关不掉的收音机》在楚天大地神一样的存在了九年,即使到今天,也教科书级般在广播界至今不曾被忘记。那个时候,我并不认识他,对我来讲,他是一个传说,直到2010年后,我们在互联网上相遇。
就在张弛明星般光芒四射的时候,他突然启动职业熔断机制,于2001年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音乐管理,2003年赴非洲加纳当了为期7个月的志愿者,同年7月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研究助理并攻读博士学位,而后成为一名学者和导师,他的名字不再张弛而武宜,这个职业将不再受限于年龄,这是他启动职业熔断机制的结果,从享受鲜花掌声的前台转到清苦寂寞的学习研究,这种熔断需要巨大的勇气,而这种熔断暂停的沉淀所积聚的力量是无法估量、令人尊敬的。
2012年3月,我随我台“百名人才招聘计划”赴武汉大学招人,就住在珞珈山脚下。坦率讲,当我以考官的身份面对朝气蓬勃、谈吐自如、思辨尖锐的青年学生时,内心是有些忐忑的,但我乐于看见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学子,他们才是未来。
 武汉大学招聘会现场
武汉大学招聘会现场
考试之余,我冒雨打车去看武汉长江大桥,途中,我接到武宜从香港打来的电话,他说,在武汉停留不多的时间里,你应该去看看夜晚的武大校园,去昙华林喝喝咖啡。是的,在夜晚的武大校园里,我看见几个同学在草坪上排练话剧,加缪的,很投入。顺着校园走进一个老式门洞,进去右拐便是女生宿舍,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樱园,我还随意走进一间教室,在黑板上点了武宜的名儿。
 2012年春天,傍晚,雨中的武汉长江二桥
2012年春天,傍晚,雨中的武汉长江二桥
 夜晚的武大,走进门洞右拐是女生宿舍,樱园
夜晚的武大,走进门洞右拐是女生宿舍,樱园
 我在武大教室里点名儿
我在武大教室里点名儿
 肃然起敬
肃然起敬
武汉,令我向往。
时间晃晃悠悠,悠悠晃晃,我所见的张武宜博士根据他的研究方向满世界穷游搞音乐节的田野调查,他的目光所及,既关乎宏大也体恤尘埃,但都不失一脚一地、一字一句的深刻报告,这是田野调查的本分。
后来,张博士定居武汉,就职于江汉大学传道授业解惑,一个功德无量的职业。间或假期,仍然各地调查研究、采风记录,我们的联系也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并不紧密,所谓淡如水。
2020年1月21日,武汉疫情严重,我发信息:五姨妈保重!而他也开始在他的个人公号《看呐人生》发布他在武汉的日常状态,平静地絮叨,我也随了他的节奏,平静地转发。非常时期,加上后来我自己不是也被居家观察嘛,纷纷扰扰的信息会干扰心绪和判断,需要过滤,我便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规划成读书、写字、做饭、打扫卫生,强迫自己屏蔽网络,只在固定的时间点通过动静APP获取新闻信息,再看看身处武汉疫区的张博士的公号,他也是有一天没一天地写,他一再强调,有话就说,没话就不讲,要讲也是讲他的亲身经历,我挺放心就没在意,也停止了转发他的公号文章。
直到3月4号,我和武宜共同的“狐朋狗友”余伟转发了一段央视英文国际频道播出的视频我才知道,就在我毫不在意的这段时间里,张博士因为轻症感染新冠肺炎、他77岁的父亲重症感染,还带有基础疾病,父子俩双双入院治疗,再后来我又在他的文字叙述里了解到他们是如何感染、住院、治愈、出院。
这期间,他除了带着父亲、带着生活必需品、带着书、带着笔记本,以病患的身份、以照顾父亲护工的身份,在医院里读书(《文本盗猎者》、《流动的图像》等等)、写公号(写他的医护、写志愿者)、给学生辅导论文、策展(桑吉加的舞蹈创作网络分享会)……在我看来,张博士因疫情再次启动熔断机制,只不过,这次他启动的是熔而不断。
 张博士住院治疗期间带去的书
张博士住院治疗期间带去的书
看了那段视频后,我在我们三个人的一个群里转发以示我知道了,并留言:祝福五姨妈,我们为你骄傲!他随即发来一张他和父亲治愈出院后的照片过来,挺精神的,我说:“等疫情过后,我要去武汉看你们!”他问:“你敢吗?”我说:“当然敢!”
 张爸爸和张博士出院后继续居家观察时所拍
张爸爸和张博士出院后继续居家观察时所拍
一场灾难,考验的是人性的善恶,因为张博士的熔而不断导致我们在当时并不知道他经历了那么多,我们以为他什么也没有说,其实他说了很多,做了很多,只是自以为聪明的我们看不见。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传来一个讯息,乡村音乐传奇歌手Kenny Rogres去世,享年81岁。
 Kenny Rogres
Kenny Rogres
他是我们生于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人欧美音乐启蒙的歌手之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歌在电台里播放。我没听过张弛的《关不掉的收音机》,但我坚信,他的节目里一定播放过这位歌手的歌。而今天,他的歌声永远留在了唱片里,留在收音机里。好在,收音机是关不掉的,我就似乎听到了Kenny Rogres烟熏过、酒浸过的,仿佛拉丝银工艺般闪烁着暗光、欲言又止的软金属嗓音在低沉地唤我:嘿!《Lady》。

Kenny Rogers - Lady
00:00 / -点击上方可听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