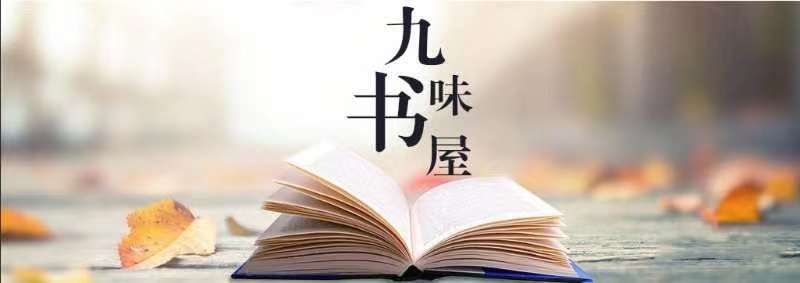
丰子恺:春
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希望它长在人间。
诗人,特别是词客,对春爱慕尤深。试翻词选,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
后人听惯了这种话,自然地随喜附和,即使实际上没有理解春的可爱的人,一说起春也会觉得欢喜。
这一半是春这个字的音容所暗示的。“春!”
你听,这个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惺忪可爱!
这个字的形状何等齐整妥帖而具足对称的美!
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想起来一定很可爱。
好比听见名叫“丽华”的女子,想来一定是个美人。然而实际上春不是那么可喜的一个时节。
我之经验,深知暮春以前的春天,生活上是很不愉快的。
梅花带雪开了,说道是漏泄春的消息。但这完全是精神上的春,实际上雨雪霏霏,北风烈烈,与严冬何异?所谓迎春的人,也只是瑟缩地躲在房间内,战栗地站在屋檐下,望望枯枝一般的梅花罢了!
再迟个把月,就象现在:惊蛰已过,所谓春将半了。住在都会里的朋友想象此刻的乡村,足有画图一般美丽,连忙写信来催我写春的随笔。好象因为我偎傍着春,惹他们妒忌似的。
其实我们住在乡村间的人,并没有感到快乐,却生受了种种的不舒服:寒暑表激烈地升降,一日之内,乍暖乍寒。
暖起来可以想起都会里的冰淇淋,寒起来几乎可见天然冰,饱尝了所谓“料峭”的滋味。天气又忽晴忽雨,偶一出门,干燥的鞋子往往拖泥带水归来。
春的景象,只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
此外虽有春的美景,但都隐约模糊,要仔细探寻,才可依稀仿佛地见到,有的说“春在卖花声里”,有的说“春在梨花”,又有的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但这种景象在我们这枯寂的乡村里都不易见到。即使见到了,肉眼也不易认识。总之,春所带来的美,少而隐;春所带来的不快,多而确。
诗人词客似乎也承认这一点,春寒、春困、春愁、春怨,不是诗词中的常谈么?不但现在如此,就是到了清明时节,也不见得一定春光明媚,令人极乐。
实际,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
就气候上说,暮春以前虽然大体逐渐由寒向暖,但变化多端,始终是乍寒乍暖,最难将息的时候。
到了暮春,方才冬天的影响完全消灭,而一路向暖。
寒暑表上的水银爬到“温和”上,正是气候最温和的时节。就景色上说,春色不须寻找,有广大的绿野青山,慰人心目。
古人词云:“杜宇一声春去,树头无数青出。”原来山要到春去的时候方才全青,而惹人注目。
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其实春工不在花枝,而在于草。看花的能有几人?草则广泛地生长在大地的表面,普遍地受大众的欣赏。
这种美景,是早春所见不到的。那时候山野中枯草遍地,满目憔悴之色,看了令人不快。
必须到了暮春,枯草尽去,才有真的青山绿野的出现,而天地为之一新。
一年好景,无过于此时。自然对人的恩宠,也以此时为最深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