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贵州西北部、毕节市南部的纳雍县,取名本有纳民雍熙之意。然而,在莽莽黔山里,深度的贫困却扼杀了无数村民向上的希望。作为贵州省挂牌督战的9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纳雍县在2016年通过“调编征兵”的方式,招聘了509名扶贫“特种兵”。四年时光,他们的战场不曾剑影刀光,却遍布荆棘;他们的战斗不曾血流成河,却暗藏坎坷。然而,心中有光,无惧路长。

大山里的杜鹃红
00:00 / -10月的毕节,迎面而来的微风裹挟着阵阵凉意,吹在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杨琴芳的身上,重回校园的她内心仍然觉得很温暖,努力读书,立志为医,这是就读助产专业的杨琴芳为自己勾画的未来。
“这个专业还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以后我在医院上班,还想开个诊所。”
 记者采访杨琴芳
记者采访杨琴芳
白衣执甲,治病救人,这是杨琴芳曾因贫穷丢失的梦想。2017年,17岁的杨琴芳初三尚未读完,就辍学去广州打工,为了一个月三千元的工资,杨琴芳站在一个牙刷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上,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9点。打工四个月后,一通电话悄然改变了她的命运。“他们打电话让我回来读卫校,是她过来带我去报名的,还给我买被子。”
杨琴芳嘴里的“她”,是纳雍县锅圈岩乡扶贫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张迪。张迪家远在赫章县珠市彝族乡,杨琴芳的家在距离纳雍县城60公里远的锅圈岩苗族彝族乡钟山村,非亲非故的两人,相识相遇的故事,还得从2016年说起。
 穿粉色衣服的为杨琴芳,曾经的她看见走访的扶贫干部都躲在一边,沉默寡言
穿粉色衣服的为杨琴芳,曾经的她看见走访的扶贫干部都躲在一边,沉默寡言
2016年,因为脱贫攻坚任务急难险重,纳雍县借鉴“特岗教师”经验,面向全国招聘509名扶贫特岗,定编在乡镇,定岗在贫困村,旨在为确保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打造一支扶贫“特军”。纳雍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忠奎介绍:“压缩县直部门的编制来倾向于基层,在全国范围内招考大专以上的学生,最后就录了509个。”
 纳雍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忠奎
纳雍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忠奎
90后的张迪就是509名扶贫特岗中的一员。当时,贵州师范大学毕业的她,看到纳雍招聘“扶贫特岗”的消息时,只懵懂的觉得这是份“稳定工作”,完全没有在意“扶贫”两字背后的重量。
考上扶贫特岗后,对纳雍一无所知的张迪被随机分配到了锅圈岩乡钟山村。原本就是从赫章大山里走出去的,她以为能适应村里的生活。然而,一次进村摸底,张迪被醉酒村民拿石头追打,性格坚毅的张迪吓得边跑边哭。那以后,晚上回到村里住处,张迪睡觉从不关灯,明亮的灯光点亮了她驻村的1400多个夜晚。“神经很敏感,一点风吹草动你都会浮想翩翩,然后就不敢睡,感觉开了灯以后比较有安全感。”
 记者采访张迪
记者采访张迪
处在峰峦叠嶂的乌蒙山腹地,深度贫困的锅圈岩乡犹如挂在半山腰上,贫困困扰着一代又一代山里人。
 张迪待过的村寨远景
张迪待过的村寨远景
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张迪扎根村里,走村串户摸查村情、识别精准贫困户、拟定帮扶措施、整理表格资料……四年来,她转战锅圈岩乡4个村,其中有全乡少数民族群众最多的土补村,也有全乡贫困人口最多的马场村,四年下来对扶贫特岗的工作有了最切身的体会:“扶贫就是你与老百姓、与真正最贫穷的人面对面,你帮这些最基层的人,把他最根本的问题解决好了,给他打一个翻身仗的问题。”
 工作中的张迪
工作中的张迪
打开张迪的手机通讯录,里面200多个电话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她村里贫困“亲戚”们的电话,杨琴芳的电话正在其中。钟山村因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资源匮乏,贫困发生率达到39.19%。这些数据,落在杨琴芳的家里,就是饭桌上常年不变的白菜洋芋。
得知杨琴芳辍学后,张迪和锅圈岩乡党委书记陈毅辗转联系到她,几番劝说,最终,是张迪陪着杨琴芳走进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今年,理应毕业的杨琴芳又选择继续读书,力争拿到大专文凭。杨琴芳说,是张迪和同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如果不是她的话,我现在可能还一直在打工吧。”
 如今自信开朗的杨琴芳
如今自信开朗的杨琴芳
因为参与扶贫特岗而改变人生轨迹的还有纳雍县张家湾镇义中村的扶贫特岗刘江。看上去柔弱文静的刘江,是纳雍县本地人,大专毕业后就离开家乡到昆明打工。2016年,刘江放弃城里生活,选择回到了家乡报考扶贫特岗,最终,选岗到义中村。“环境我心里面有准备的,但是对于工作这块,我不知道它的难度有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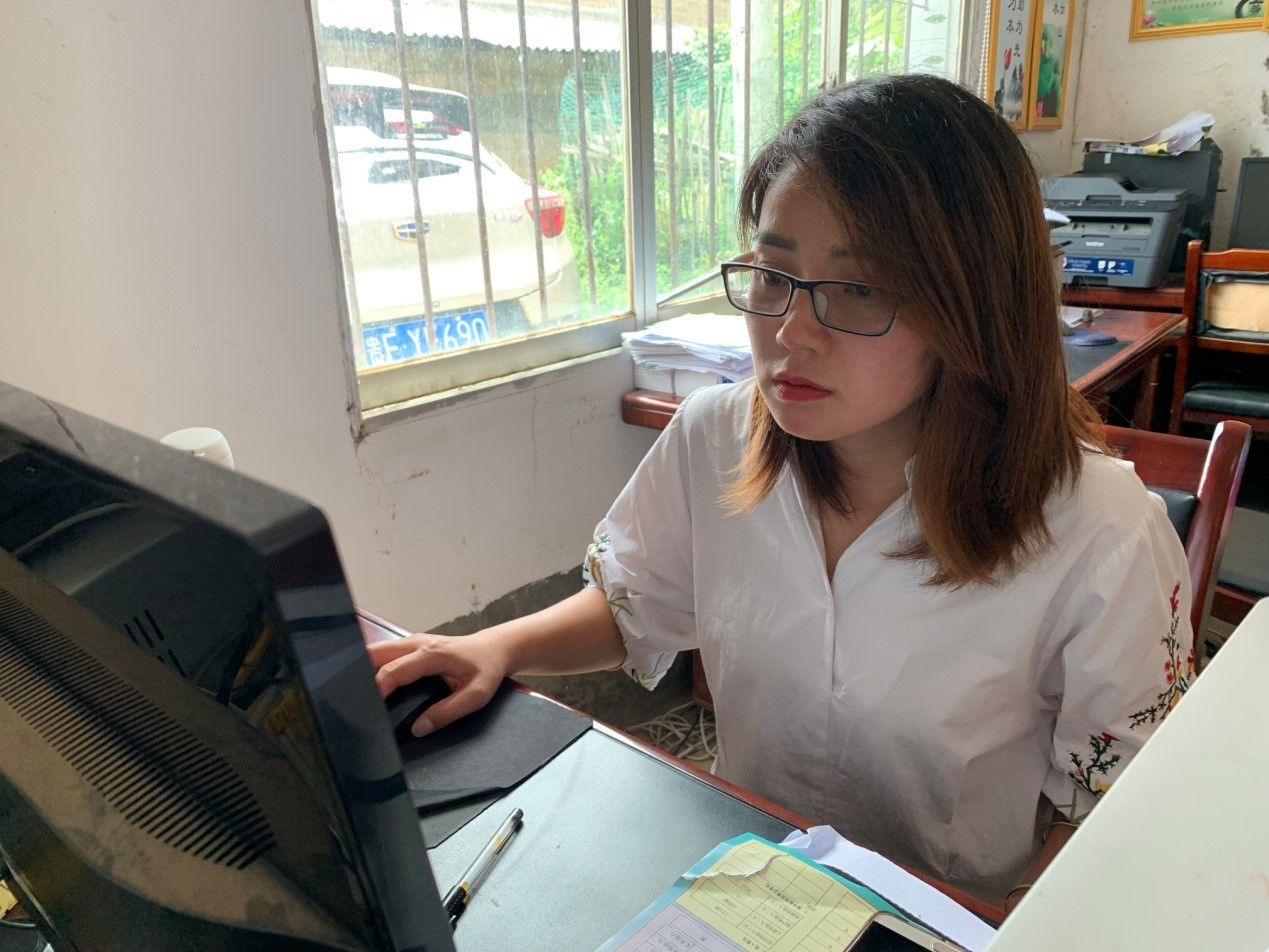 工作中的刘江
工作中的刘江
挨家挨户识别贫困户,告知扶贫政策,有问有答,村民办事,有求必应。在刘江来到义中村之前,村里唯一一台电脑落满灰尘,无人会用。刘江到来后,慢慢补齐了所有扶贫相关电子档案和资料。
扶贫特岗的苦,刘江一一咽下,然而女儿出生后,刘江却两次动了辞职的念头。“宝宝4个月的时候去重庆,确诊了是全面性的发育迟缓。到现在孩子已经三岁多了,走路不是特别稳,不会说话。”
一方面是女儿需要漫长的康复治疗,治疗效果尚未可知,一方面是脱贫攻坚刻不容缓,工作繁忙分身乏术。为母则刚的刘江,和丈夫商量后,将自己每月4200的工资拿出4000元,请人在县城帮忙照顾孩子,自己则咬牙坚守义中村。“既然参加脱贫攻坚的这个战争,这份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以后大不了我陪我女儿一辈子,她走到哪我走到哪。”
 刘江正在帮村民安装简易家具
刘江正在帮村民安装简易家具
孩子是刘江心里触碰不得的柔软,而年龄则是厍东关乡扶贫特岗蔡灿不愿谈及的话题:“刚参加工作那会有人问我有没有20岁,第二年就问我有没有30岁,这个工作真的是催人老,两边都有很多白头发。”
蔡灿是纳雍厍东关乡长坡村人,2016年从天津城建大学本科毕业后,25岁的他放弃了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选择回到家乡。而全班35人中,只有他一人回到农村。
“本来我可以留在那边,当时我跟一家公司谈了,通知我去签合同,但我想到还是得回来,帮助跟我一样贫困、一样落后的家乡。”
 采访蔡灿
采访蔡灿
厍东关乡是典型的深山区石山区,年迈父母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刨出一家人的口粮以及蔡灿姐弟三人的学费。清水煮白菜是蔡灿求学路上的常见菜肴,国家的助学贷款则是他读完大学的保障。回望当初求学路上被贫困所扰的自己,蔡灿下定决心让这样的事得到改变。
定岗到厍东关乡后,蔡灿第一件事就是申请自家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摘帽。之后,蔡灿走遍了厍东关乡10个行政村、92个村民组。帮扶的村民,很多是他曾经的小学同学。“各种各样的工作你都会涉及,留守儿童、汛期防汛,冬天防火。平均下班时间是12点,没有周末。我家离这里骑摩托车5分钟就到了,但是我十天半个月不回家一次。”
身在扶贫工作站,蔡灿的工作多了一份上传下达的使命。特别是各个村寨汇聚而来的扶贫项目申报整理,占据了蔡灿不少的时间。厍东关乡宣传委员付琳说:“我们的脱贫项目,特别写脱贫资金申报方案,扶贫工作站是扛了大头。有些涉及到比较专业的东西,比如要修个圈,要修好高?单价是多少?基础要挖好深?这些都要写进方案里面去。这当中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
千头万绪的扶贫工作,没有压垮蔡灿,然而当初一同定岗厍东关乡的18人,已经有4人辞职。而纳雍全县509名扶贫特岗,大浪淘沙后已解聘131人,淘汰率达25.7%,剩下的378名“特军”则转为正式编制,其中,有371名“特军”担任了村干部。纳雍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忠奎说,扶贫“特军”点对点联系贫困家庭,精准管理贫困户信息,直接服务全县5.6万户24.7万多贫困人口。四年来,纳雍共促进15.5万名贫困人口有效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8.05%下降到2.95%。
对于扶贫特岗的作用,张忠奎这样评价:“打仗都是要有士兵锋陷阵,最优秀的最得力的是这帮人。喊他们脱贫攻坚‘特种兵’当之无愧。”
在脱贫攻坚的战场,刘江依旧忙碌在义中村里的每个角落,帮助村民办理户籍、组织村民打扫公共卫生,联系学校培训种植技术……4年时间,她参与并见证了一个贫困村的蜕变出列,但喜悦的背后,总有遗憾。“最大的遗憾还是孩子,我没办法陪在她身边。有时候我晚上回去,她就一直哭,有点像忘了我。我也哭了,感觉连我家孩子都不要我了。”
蔡灿每天还忙于各项工作,从县到乡,从乡到村,上传下达的他,需要做各种资料收集、表格统计、项目申报……而白发苍苍的母亲,开始为29岁的他催婚。对于母亲的唠叨,蔡灿充耳不闻,一心盼着脱贫攻坚考核验收结束后狂欢一场。“等哪天验收过关了,我们彻底脱贫了,狂欢三天。”
 蔡灿
蔡灿
外来人张迪已经成长为锅圈岩乡村民口中的“幺姐”,哪家几口人,哪家几亩地,她一清二楚。家乡赫章反而成为了回不去的远方。
《彝山杜鹃红》,这首在家经常唱的山歌成了张迪思乡的慰藉,婉转歌声里,有她作为扶贫特岗的骄傲和自豪,一如歌曲中火红的杜鹃花。“扶贫特岗这个词,可能以后很少有人提,但扶贫结束了以后,还会有乡村振兴,我们的工作也会一直做下去。”
 张迪结婚,杨琴芳送上祝福
张迪结婚,杨琴芳送上祝福
(贵州综合广播 谢红娟 黄静 张勤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