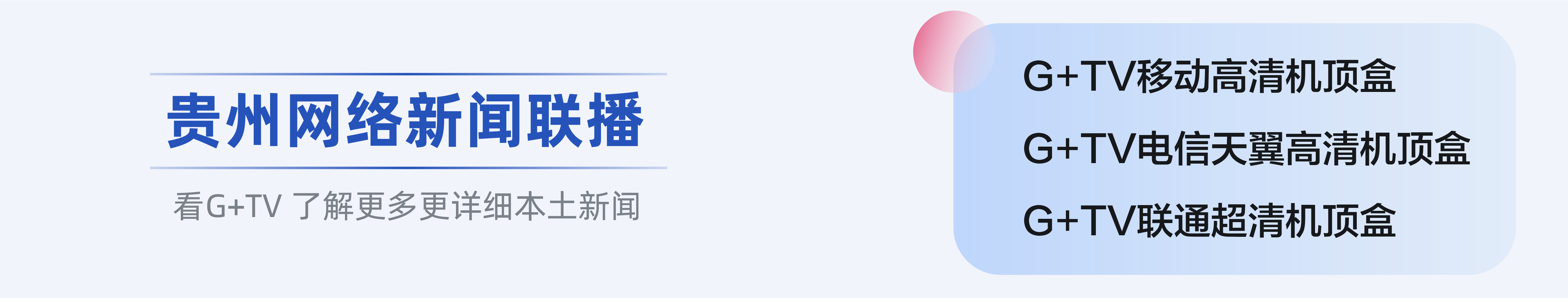天还没亮透,世纪城的路灯还裹着雾气,刘姐的三轮车已经支棱在街角。两个老甑子蹲在铁皮箱上哈白气,糯米香追着晨跑的年轻人跑出半条街。她戴着毛线勾的露指手套,虎口掐出圆润的弧度,脆哨碎像雪花似的飘进凹槽。“要辣椒不?”这声贵阳清晨的暗号,二十年都没变过音调。
那天下着大暴雨,我钻进刘姐支起的透明雨棚。水珠顺着塑料布淌成小河,她忽然指着保温桶上褪色的小熊贴纸:“小王,你看这个!小浙江当年在我饭盒上贴过同款。”糯米蒸汽腾起来,二十年前的往事在潮湿空气里慢慢回潮。



2002年的三桥批发市场,十八岁的刘二妹推着板车送干辣椒。总有个浙江口音的货车司机,卸完货还要蹲在档口数麻袋。“强哥,你数第三遍了。”她递过搪瓷缸,茶叶在开水里翻跟头。男人从工装裤兜掏出个玻璃瓶:“这是我们宁波的烤麸,你配酸萝卜……”话没说完就被进货的人潮冲散,只剩个红耳朵尖在人群里晃。
情人节那天,茶叶铺的小开送来裹着红绸的银镯子。刘二妹正发愁怎么还礼,阿强喘着粗气冲进来,怀里抱着的海鲜面还沾着冰碴。“这个煮汤鲜得很。”他低头盯着自己开胶的劳保鞋,“面是碱水面,经煮。”后来那些追她的后生都不知道,打动姑娘的从来不是花哨礼物,而是冰天雪地里护着面条的那双手温。


真正定情是在暴雨夜。阿强打着手电带她钻进货车厢,光柱扫过两个倒扣的塑料筐,旧棉衣铺成的“沙发”上摆着饭盒,泡烂的海鲜面胀成胖月亮。“我嘴笨,但会修车会煮面……”话没说完就被棉衣砸了满脸。后来车头贴满草莓贴纸,他说这叫“莓烦恼”,她也偷偷在方向盘系上苗绣平安符,针脚歪得像蚯蚓。
爱情的分岔路出现在2004年春天。老家来信说要开物流公司,阿强把存折往她围裙兜里塞:“跟我去宁波,咱们开个面馆。”刘二妹攥着存折没松手,那上头每一笔都是留着帮母亲开糯米饭摊的。当货车尾灯消失在晨雾里时,她保温杯里的羊肉粉还烫手。


去年同学会,当年批发市场的姐妹还在唏嘘:“刘二妹,你说这强哥要是不走……”刘姐往对方碗里添了勺油辣椒:“哎呀,现在我家老周,天天四点起来帮我泡糯米呢。”转头看早餐车旁,穿快递员制服的男人正给煤气罐缠防冻布——这是十年前相亲认识的实在人。
清晨去买糯米饭,正赶上刘姐教闺女包引子馅。小丫头把花生碎撒成个月牙笑脸,乐得直晃羊角辫。老周闷头在旁边忙活,把油辣椒分装成小包,特意留出单独一袋——袋口拿红油画个小太阳,这是专门给忌口的王嬢留的。糯米蒸腾的热气里,晨光给这一家子镀了层暖烘烘的金边,连案板上滴落的红糖都甜得透亮。


或许世间缘分就像刘姐手心的糯米饭,年轻时总想包进星辰大海,后来才懂珍贵的是经年累月捂热的寻常。那些消散在高速公路上的诺言,到底变成了孩子们咬到糖引子时惊喜的“哎呀”声。
作者/摄影:王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