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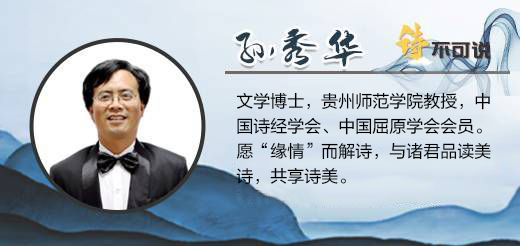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一名句出自北宋苏轼《临江仙•送钱穆父》: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钱穆父是苏轼的友人,即钱勰。《宋史》卷三一七《钱勰传》载云:“勰字穆父,彦远之子也。”钱穆父出身名门,是吴越钱王的后裔,宰相钱惟演的从孙。这首词作于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春,时苏轼知杭州,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知瀛洲(治今河北河间)途经杭州的老友钱勰钱穆父而作。
词作的大致意思是:京城一别,我们已三年未见,你我总是远涉天涯,又辗转在人世间。相逢欢笑,依然像春天般温暖。君心始终如古井,不起波澜,你高风亮节,似秋天的竹竿。心中难免惆怅,因你连夜就要扬帆远航,送行之时,云色微茫,月光淡淡。送别宴席上,歌妓却也不必端着酒杯愁眉不展,为离愁别恨而哀怨。人生如同在客舍旅店暂住,我也是匆匆过客啊。
词作上片写与友人久别重聚,赞赏友人面对坎坷奔波时的古井心境和秋竹风节。下片先写月夜与友人分别为衬托,抒发了对世事人生的超旷之思。词写眷眷惜别之情,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全词新意横生,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
元祐初年,苏轼在朝为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气类相善,友谊甚笃。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钱穆父出知越州时,苏轼曾赋诗二首赠别。
苏轼《送钱穆父出守越州绝句二首》诗云:
簿书常苦百忧集,樽酒今应一笑开。
京兆从教思广汉,会稽聊喜得方回。
若耶溪水云门寺,贺监荷花空自开。
我恨今犹在泥滓,劝君莫棹酒船回。
钱穆父是能吏,此前曾“迁给事中,除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这所谓“权知开封府”实际为“代理首都最高长官”,即苏轼诗中所称“京兆(尹)”。世人皆以当京官为尊贵,今钱穆父出守越州而苏轼送别有贺喜之意,并自称还“不得外放”是“我恨今犹在泥滓”,二人心意相通,惺惺相惜。又因为钱穆父是吴越武肃王钱镠的六世孙,所以现在“钱穆父出守越州”,这在苏轼看来很有穆父回到“故国故地”之“喜”,这一点也是苏轼这两首赠别诗暗含的意蕴。
苏轼豪放达观,越是逆境,越是超然物外、随遇而安。写《临江仙•送钱穆父》词此次会面钱穆父之前,苏轼有诗《和钱四寄其弟和》诗曰:
再见涛头涌玉轮,烦君久驻浙江春。
年来总作维摩病,堪笑东西二老人。

钱穆父排行第四,苏轼称他为“钱四”是较为亲近的说法。诗句“烦君久驻浙江春”表明,其时钱穆父或正当在越州知州任上。
而一别三年,“天涯踏尽红尘”。苏轼称赞友人钱穆父“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初心不改,保持耿介风节。追根求源,“古井秋竹”这个说法来自唐代的著名诗友“元白”,白居易与元稹。白居易《赠元稹》诗曰:
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
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
岂无山上苗,径寸无岁寒。
岂无要津水,咫尺有波澜。
之子异于是,久处誓不谖。
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
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
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
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
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
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
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
白居易赠好友元稹的原诗句有“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苏轼化作“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对友人的肯定还要更进一层。又,白居易此诗中有“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之语,这与苏轼写给钱穆父词中的“一别都门三改火”,也暗暗相合。
分离日长,相见匆匆,月夜又别。于是,感慨系之矣!词的下片切入正题,写月夜送别友人。凄清幽冷,抑郁无欢,情景类似白居易名作《琵琶行》诗句所歌:“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临江仙•送钱穆父》词情感与思想的升华就在这结语二句。名句的直接来历应该是唐代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逆旅”一语,唐人早已频频入诗。如,唐代刘长卿《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诗有曰:“逆旅乡梦频,春风客心醉。”刘长卿该诗也有“见君风尘里,意出风尘外”,以及“一片孤客帆,飘然向青霭”之语,情味也与苏轼《临江仙•送钱穆父》词极其相符。而苏轼名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渊源,实则可追溯至《庄子·知北游》之语:“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苏轼对庄子此语当然了然于胸,很是喜欢。苏轼《雪后至临平,与柳子玉同至僧舍,见陈尉烈》诗有云:“大哉天地间,此生得浮游。”又,苏轼《迁居临皋亭》诗开篇便说:“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

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聚散和江南江北呢。而实则苏轼不但早明确就有“人生如寄”之叹,且还曾写给了友人钱穆父。苏轼《西江月·送钱待制穆父》词云:
莫叹平原落落,且应去鲁迟迟。与君各记少年时。须信人生如寄。
白发千茎相送,深杯百罚休辞。拍浮何用酒为池。我已为君德醉。
果真,“须信人生如寄”?
苏轼这首词,当与其《送钱穆父出守越州绝句二首》诗作于一时,皆是送别“钱穆父出守越州”饯别宴会上的歌吟。又苏轼《答吕梁仲屯田》诗亦有曰:“人生如寄何不乐,任使绛蜡烧黄昏。”
在注定漂泊的境遇中,我们又如何“自适”呢?
而实则深沉感慨人生如寄,“五言之冠冕”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是尤为集中和突出的。《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有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歌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有曰:“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而《古诗十九首》自当是历代文人的“必背篇目”,其中反复吟唱的“人生如寄”之飘零无依,慷慨悲凉,感人至深,苏轼也必定会从中精心学习揣摩。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这一千古名句,洗脱了悲戚之情,挥洒着昂扬豪迈,既清醒揭示了人生真相,又温柔以待,能给你从容前行的勇气。这种智慧恰如暗夜中的灯盏闪亮,又仿佛轻声述说——你我并不孤独,众生皆在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