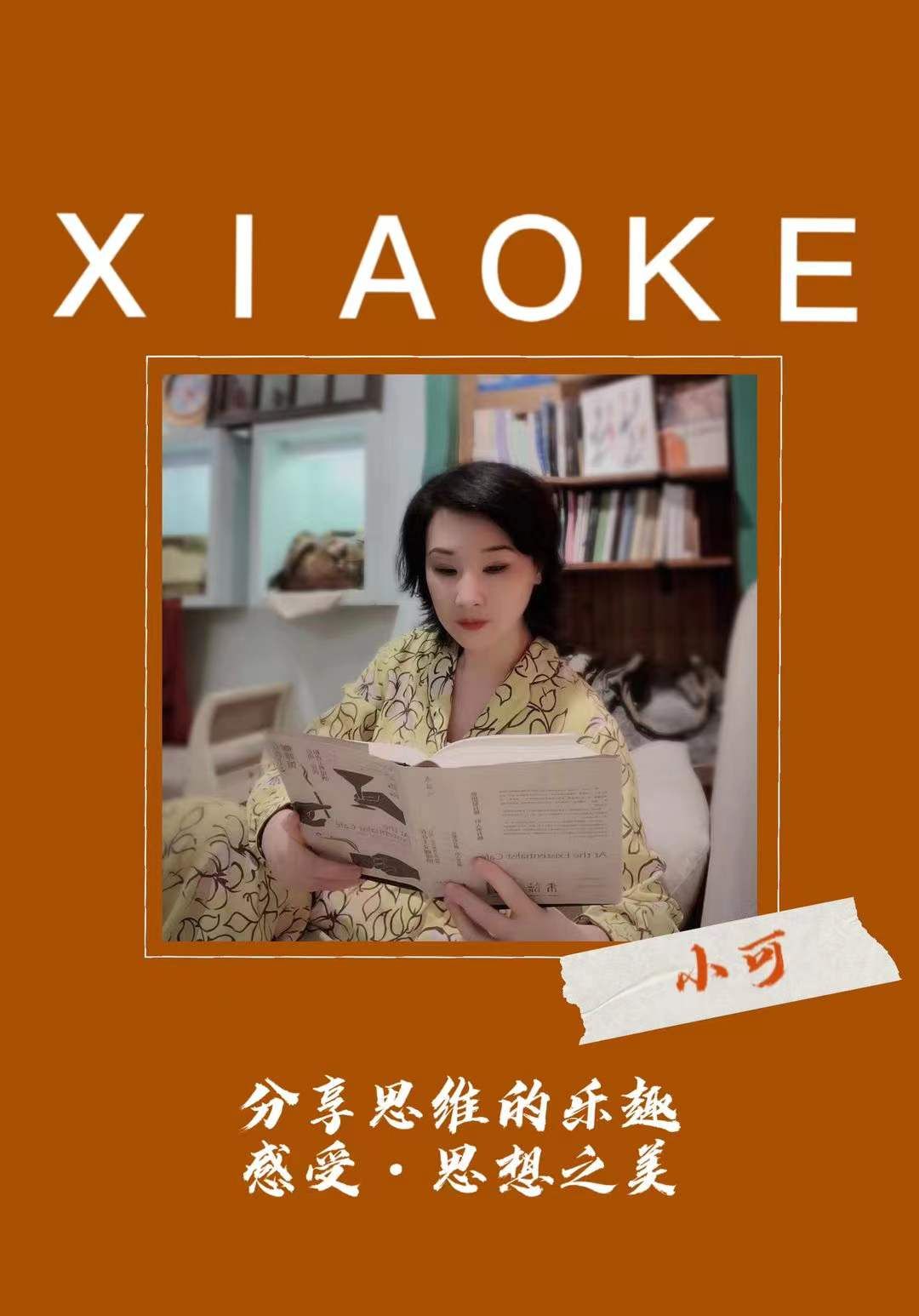2022年初,热播电视连续剧《人世间》,将一位在文坛深耕五十年的“老”作家梁晓声重新拉进了大众的视野。自1972年发表首篇文学作品以来,梁晓声一直笔耕不辍,且创作内容涉猎广泛,各种体裁都有广为人知的代表作,还在2019年凭借《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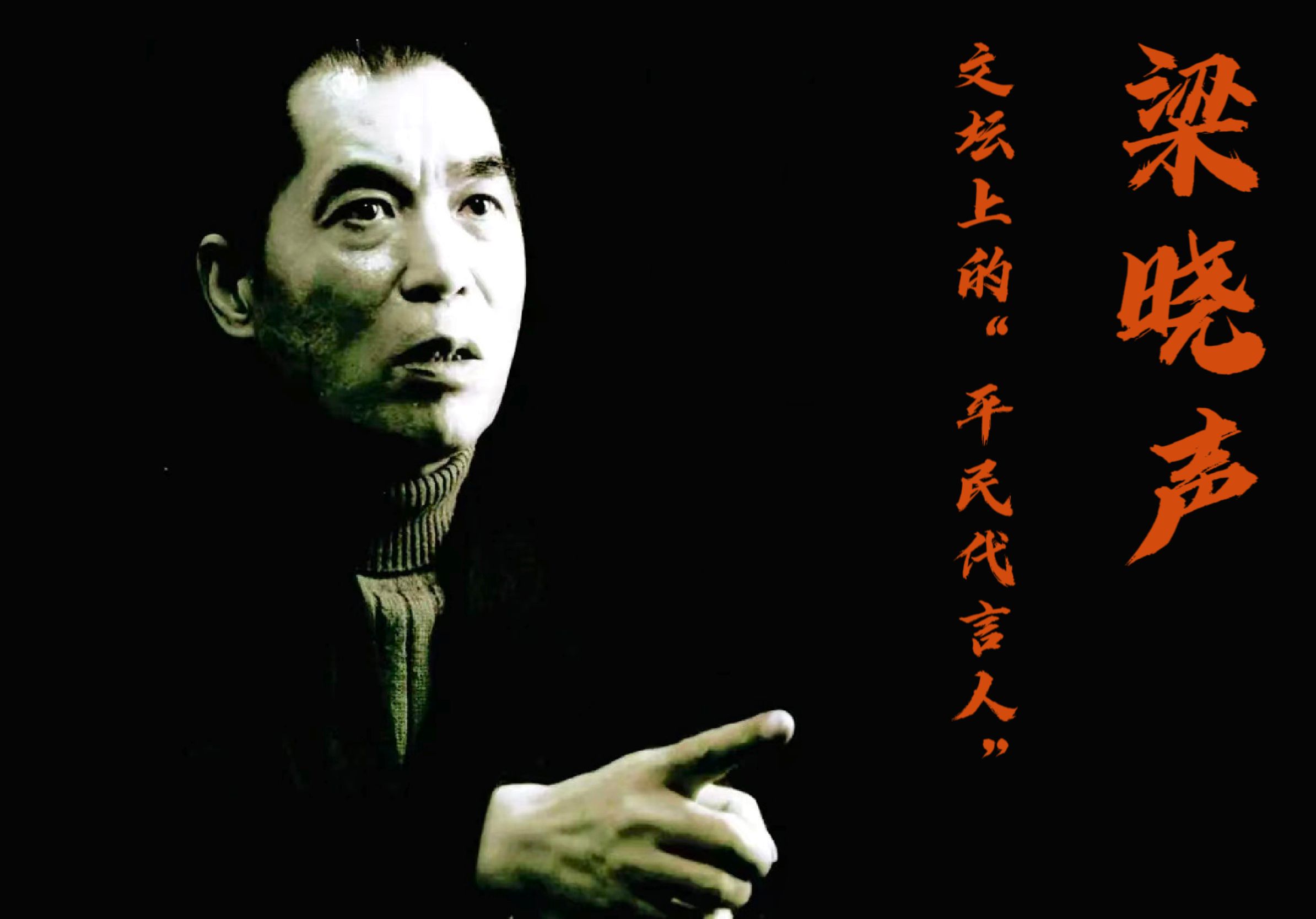
文学具有引人向善的力量
梁晓声的作品大多是反映普通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作品中的人物原型也大多出自他自己、家人以及身边的朋友们。他曾经说过,写作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他认为没有作家能够仅凭经验和技巧,就能把自己并不相信的价值观写出来,能写出来的,一定都是发自内心的表达。
有读者说,从梁晓声的作品中,能读到崇高,这在今天实属难得。而这份难得恰是因为梁晓声的文学创作理念:“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给人以精神的滋养,人类归根到底需要文学,还是它促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品格上提升、再提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学才和人类发生联系,它具有引人向善的力量。”
他始终对文学保有一颗敬畏之心,一直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向现实主义致敬,通过他笔下不同层面的人物,传达他对社会的感知和愿景。“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遇又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比较能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有时,仅仅是一种而已。”
正是凭借这种坚定、执着的人生信念,怀着清醒、坦然的处世态度,梁晓声这五十年来,将自己的所长发挥到了极致,创作了两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图书近百种。他的笔下书写了五十年来新旧嬗变的时代,他的作品展现的是一代代中国人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与热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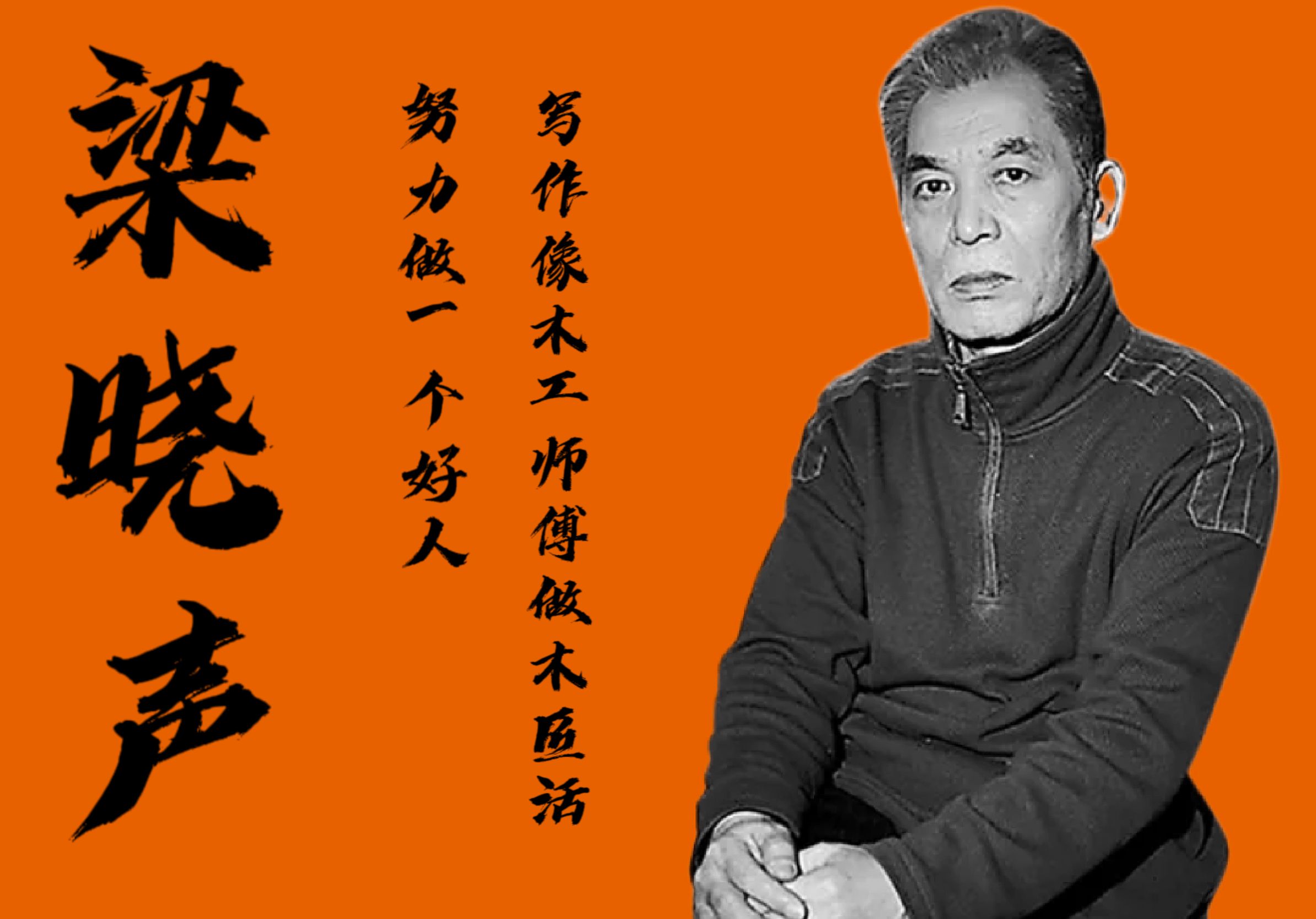
努力做一个好人,写作像木工师傅做木匠活
作家最初所接触的作品往往影响到他成为作家之后偏向于哪一类作品。梁晓声受俄罗斯文学影响比较多,俄罗斯文学有一个时期强调塑造“新人”——一个人的一生,总是要尽量地为他的国家、为他所处的时代,做一些超越个人情感和个人人生价值的事情。
其实和当年蔡元培先生对于北大学子的愿望是相近的。而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也说过: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才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的经历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他们的作品里其实也谈出了“好人文学”的理念。这个“好人文学”不是我们常说的“老好人”,它是指,无论外部因素是怎样的,人在最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是如何坚持自己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立场,比如说同情、帮助、竭力地坚持正义。
写作非常像木工做木工活,或者一个老的面点师傅做面点,也非常像裁缝和鞋匠做衣服鞋子。即使一个老裁缝已经决定退休了,金盆洗手了,可是他打量一下自己的裁缝案子上还有布料的话,他可能心里还在琢磨怎么样再把这块布料做一下。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梁晓声总是想结束写作这件事。但是在有此念的同时,确实也会有新的素材进入。就像老鞋匠经常有人找上门,对于作家来说就是约稿,约稿有的时候还伴随着友情,比如说和这个编辑的友情;有时则是由于现实生活中新的事件、新的形态冲击到自己了,于是又觉得还不能休息,还要继续写下去。

“最后一部”确实是最后一部了。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放下笔,不再写作,也不再想文学这件事,也不再保持和文坛包括出版界的过于密切的关系,然后可以到各个美丽的乡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最后一部”的历史跨度更长,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写到九十年代初,写了四代人。我之所以要写这,是由于一本很厚的书,差不多一千页,是我的母亲城哈尔滨编的《哈尔滨编年史》,就从最初的松花江边的那几户人家的起点开始一直编写。
我是有英雄崇拜情结的。就是现在,看纪录片还会有一种感动——在那个时候,我们志士们,为国家、为民族所做出的牺牲。可是我本身没有写过这方面,所以这“最后一部”就是为自己圆了一个情结。
——梁晓声
文本参考:长江日报 读+周刊 记者:李煦 《我最后一部长篇要写“四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