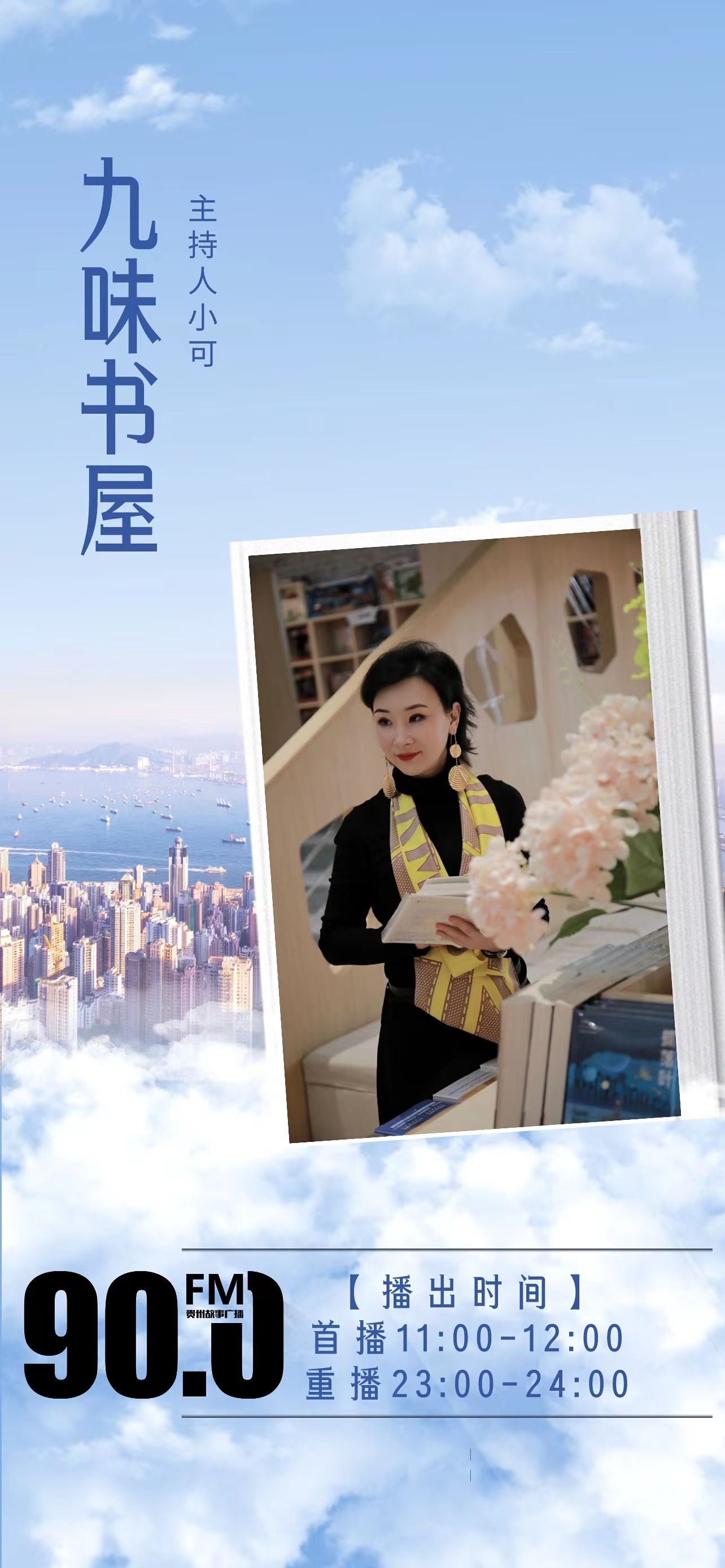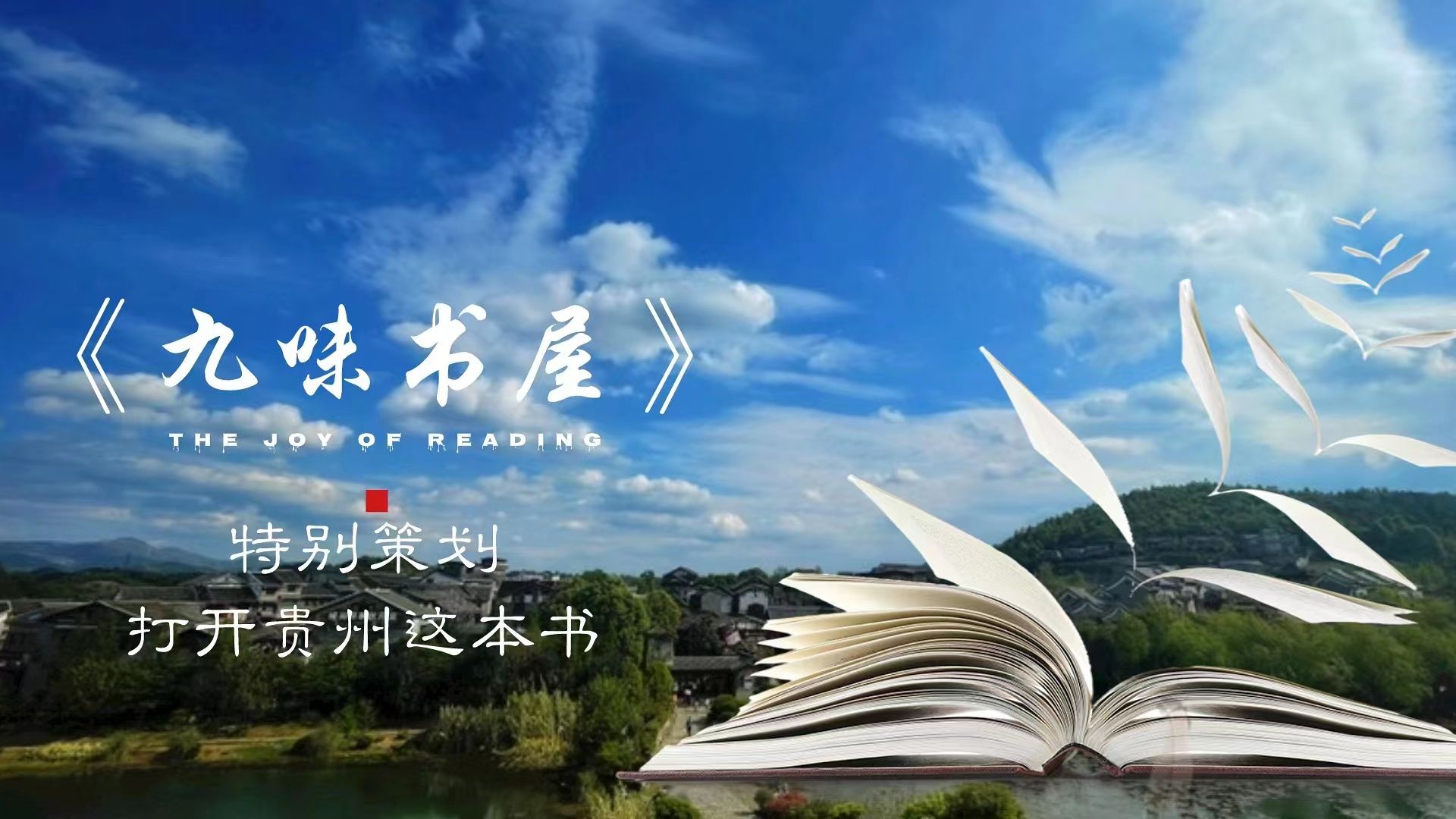
高原的容貌
作者:叶辛
高原的容貌,就是大山的面貌。
大山的面貌,和人一样,往往也决定了大山的性格。
大山也有性格吗?对于生活在大山里的民族来说,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生活在太行山上的人们,有太行人的性格;生活在吕梁山上的人们,有吕梁人的性格。同样,对于生活在东北大兴安岭山村里的人们;对于海南岛上五指山麓的人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性格。
云贵高原同样如此。
云贵高原上有几十个世居民族,这些民族性格的形成,都和云贵高原千姿百态的山山岭岭有关系。而这些性格,又是同高原特有的容貌分不开的。
广而言之,去往美洲的落基山脉,到达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和那里的山地民族沟通、交流,你会发现,他们也都会有各自的性格和风貌,而这些性格和风貌的形成,又是同大山的面貌分不开的。

那么,云贵高原上大山的容貌,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和贵州的山地结缘50多年,天天感受着大山的风霜雨雪,观察着大山面貌的变幻,和大山的性格展示,接触着世世代代栖息在大山怀抱里的民族,你可以用很多形容词来描绘高原的容貌。
大雨滂沱、形成咆哮山洪的时候,大山是一种性格。风和日丽、气候温润祥和的春天或是中秋,大山又是一种性格。变幻无常却又并非规律不可寻的种种性格,形成巍峨的、指天戳云的、形状各异的各种山岭景象,这一景象决定了栖息在云贵高原上各个世居少数民族的性格。
无论是哪一个民族,要在云贵高原上寻觅到一个地方栖居下来,躲开喧嚣隐居下来的汉族也好,避开战乱、灾难、迁徙而来的各个少数民族也好,其首要的条件,是得要能生存下来,而生存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有水。
水能解渴,水还能润泽土地、催生万物。逃难而来的各族祖宗,随身会携带各种各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所有的必需品中,种子是必不可少的。有了水源,种子栽进泥土里,就能发育生长,就能种出粮食,让人得以生存下来,生命得以延续繁衍。

所以在各个少数民族以歌传史的演唱中,古歌中都会从他们的祖宗如何寻觅到这一山清水秀之地唱起,唱到山林的茂密,唱到环境的幽雅宁静,唱到土地的肥沃盛产,唱到世世代代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山的感情。
在世代栖居的岁月中,他们熟悉着大山,依赖着大山,也在开垦和发掘大山的过程中,和大山形成了和谐共处的默契。当大山暴怒时,他们容忍着暴雨、暴晒带来的水灾和旱灾,他们适应着大山带给人们的灾祸,只因大山是他们的家园,是赖以生存的栖息地。
故而走进云贵高原最为偏僻的村寨,人们都会发现村寨附近有一股水,这股水或是清澈的山泉,或是淙淙潺潺流淌而来的溪河,或是从喀斯特山地特有的洞子里淌出来的阴河里的水。哪怕这水再凉、再冰,人们都会有办法将其变为有利于自己民族的生存之水。
在贵州,有一句话形容少数民族的栖居之地:“苗族住山头,布依住水边。”

作为人数最多的贵州两个少数民族,以表面上他们栖居村寨的形态看,这一句俗谚没有错。
但是只要来到苗岭深处,来到清水江两岸,就能发现,乍眼看去,耸立在高高山巅的苗寨,其在这边的一条一条石阶路,都能通到静静流淌的清水江边。
其实,何止是布依族、苗族,走进侗村,来到水族寨子,包括毛南族、瑶族等在内的所有世居贵州的少数民族,都爱在水边居住,都离不开这一生命之源。
山地上的水滋润着高原的容貌。正因为处处都有水,高原的容貌才会变得郁郁葱葱,才会变得青山碧岭,才会形成高原独特的山地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