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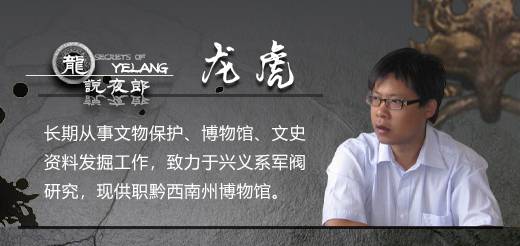
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安龙国家山地户外运动公园(国际攀岩公园)位于风光秀丽的笃山镇梨树村海尾山谷,顾名思义,海尾不仅是一个山谷,而且是一个水资源异常丰富的山谷。一条是自西向东流淌的筏子河(今下游改名坝子河),水量较大,河水陡然伏入公园内巨大崖壁下的落水洞。一条是石冲河,从西南向东北流淌,穿过公园的入口倒马坎。贵州多山,地名“倒马坎”尤为常见,引申出来的传说五花八门,然而,共同的特点是地形危险,悬崖很高,牛、马和牲畜很容易掉下去。石冲河的源头位于普坪镇的大鸭溪水库,终点是梨树村的张家桥组,全长约17公里,与筏子河相比,水量相对较小。因此,《兴义府志》记载了筏子河,但没有记录石冲河。历史上,有一座古桥建在流经倒马坎的石冲河上。今桥毁无存,但保留下三座建桥石碑,其中两座为四棱碑。碑文内容“一桥三名”,历史脉络被清晰记载下来。
 安龙国家山地户外运动公园巨大崖壁
安龙国家山地户外运动公园巨大崖壁
第一座四棱碑立于“道光十一年(1831)季冬月(农历十一月)”,时任兴义知府为徐玉章。四棱碑三面镌刻,碑面残损,能辨识部分文字。正面额题“永镇桥”,开头便是“尝读帝君文曰”,即经常读《文昌帝君阴骘文》,教导我们“修道路以利人行,造河桥以济人渡”。尽管“者都之厂河虽非四达”,就是不算特别重要的交通要道,但也是两岸乡人往来的必经要地。碑文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这里古名为“者都”,二是今天的石冲河当年老百姓称为“厂河”。“者”在布依语音中比较常见,意思是“山上的平地”。“厂”则是指山崖,“厂河”就是山崖下的河流。更重要的是,四棱碑和志书能够相互印证,今天的梨树村倒马坎,正是《兴义府志》记载的“北乡永化里四十六寨”之“者堵寨”。
 “永镇桥”四棱碑
“永镇桥”四棱碑
碑文接着描述,奈何“独木难支,于是募化场市、乡村、厂号人等”,共同建桥。文中还穿插“遥通帝座,百福普播,虎生庶兑,培风檀水”等生僻的佛、道吉语。按照惯例,文末为桥“今功成完竣,以志不朽云”,但撰文者未留名。碑文记载共有五位“首领(向德、陈锦文、韦朝富、贺尚贵、杨荣)”助钱“卅(三十)斤、廿(二十)斤”不等。换算一下,清代一斤为16两,一两10钱,一斤即160钱。道光年间,一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相当于这些首领助银三两到五两左右。“首领”之下为“众善”助钱。四棱碑的左右侧面,亦全部为“众善”捐款,其中以王、贺两姓最多,结合“者堵寨”地名,可以判断该地百姓以布依族为主。
第二座四棱碑立于1967年12月,三面镌刻。正面题“群心桥”三字,碑额用印刷体镌刻“毛主席语录”,内容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讲话,今天我们依旧传承着这一思想。群心桥名之下,镌刻洋溢时代特色的建桥原因,原文为:“道光十一年人民为了通行渡河发展生产,经众自筹经费建成永镇桥。可是,万恶的封建势力、地主豪绅为了掩盖他们的剥削罪恶,用思想迷惑群众自由,于光绪十四年将此桥破坏,使人畜安全受到无故损失。在那种社会里,有冤无处申。解放十八年来,广大贫下中农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下文字残损,但原因一目了然,就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桥梁被毁。当然,毁掉的原因大概率还是自然原因,而不是碑文所述被“封建势力、地主豪绅”人为破坏。
 “群心桥”四棱碑正面拓片 黔西南州博物馆藏
“群心桥”四棱碑正面拓片 黔西南州博物馆藏
这座四棱碑两侧面同样为建桥捐款内容,只是从道光年间的“众善”,换成更具时代特色的“社员献金名单”和“集体献金单位”。社员来自合星生产队和洒雨区天兴、岩脚。“集体献金单位”有三个,分别为合星生产队、胡家坪生产队和张家营生产队。合星生产队献金最多,捐款631.88元和大米300斤。这些地名均在梨树村及周边,目前胡家坪和张家营两个地名尚存,为村民小组。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座四棱碑捐款人以王、贺两姓布依族为主,而这座四棱碑增加了陈、刘、龚、向等汉姓,民族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
第三通碑为青石质,额题“永兴桥”三字,石材厚度达20厘米,立于1979年十月初四(11月23日)。因“洪水暴涨,水势凶猛”,群心桥于“旧历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冲毁,“往来行人过河又受困难,生产遭受影响。但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下,各级党委的大力支持,国家补助资金一千八百元”,桥于“旧历七月七日动工,十月初建成。”除国家补助,建桥的“集体献金单位”和第二座四棱碑完全相同,分别为合心、胡家坪和张家云生产队,只是用字略有区别。另外,这次建桥没有记录群众捐款,而是“以工代赈”,由合心、胡家坪两个生产队组织群众自行修建。“集体献金”全部用粮食替代,仍是合心生产队最多,为大米515斤,包谷220斤,黄豆50斤。胡家坪生产队其次,为大米187斤,包谷80斤。张家云生产队最少,为包谷300斤。原因是三个生产队使用桥梁的频率不同,张家云生产队距离桥最远。
 “永兴桥”石碑
“永兴桥”石碑
山地贵州,被誉为“世界桥梁博物馆”,像这种“桥毁碑存”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些石碑不仅为贵州建桥史添砖加瓦,同时附带出的历史信息,对研究地方社会的时代风貌,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