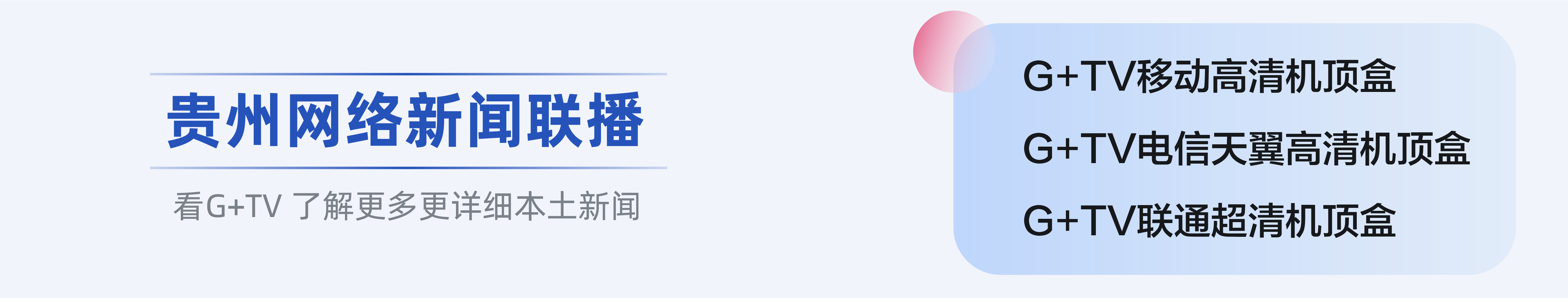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贵阳小吃中,与鸭子有关比较重要的,除香酥鸭,便是鸭块面了。
但鸭块面在本地并非流行很广,有名者仅“刘半夜”、“田福记”等寥寥几家而已。面亦平平无奇,用材做法与肠旺面相近,但鸭子烧得硬是不赖,一大块切将下来,铺在面上,撕咬一通,豪气陡生。

早年间,“刘半夜”几乎一枝独秀。鸭块面之外,还经营各色卤味,鸭肠、鸭肝、鸭胗、鸭脚、卤蛋、豆腐、花生……佐酒最宜,打完几圈麻将的夜猫子,晃过来整几瓶夜啤酒,安逸得很。与“半夜”的名实相符,通宵营业,生意也便兴隆。唯不见卖脖子,不晓得是不是专供油炸香酥鸭去了。这几年,“刘半夜”好像突然不见踪影,据说已经关张,反正我是没有打听到搬迁的信息。
另一家相距不远,在万东桥下,即前面提到的“田福记”,单就鸭块面的味道来说,似乎还胜出一筹。此外,还有火爆鸭、鸭杂面等飨客,我印象中营业时间较短,下午便收摊。

鸭块面
贵阳做鸭子有名的,我所知道,还有一家“天维地”的酱鸭。十几年前,大十字老百货大楼卖的酱鸭极好,是什么品牌已不复记得。家里来客人,一时菜不够,老爷子往往就要叫我去砍一只或半只回来吃吃。回想起来,“天维地”酱鸭的味道就与之仿佛,偏咸而鲜,入味,佐酒想必不坏,可惜我不善饮。如今久未上门,也不知还在不在?
鸭子是老的好。
老鸭煲汤,味厚而甘,非三五碗下肚,不得餍足也。而年齿尚稚者,煮出来一股子怪味道,骚腥不能入口。
鸭系温补,自古就是中国人菜单上的常客,吃法多样,不时翻新。但似乎选材还真得有所注意,清人曹庭栋撰《养生随笔》引《禽经》云,鸭子一物,“白者良,黑者毒;老者良,嫩者毒”。啧啧,已经上升到“毒”的高度,不单单味道不佳而已。
遵义某友,跟我同好,也不爱吃鸭子,总觉得有股特殊的气味,“说难听点,就是鸭屎气。但确实有些厨师妙手,能让鸭子变得让人欲罢不能,除了酸萝卜炖的老鸭汤,就数绥阳蒲场镇章水饭店的卤鸭子了。每次回老家绥阳必吃无疑,还要带一两只走人。但我的食用原则是:不吃热的,只吃凉的”。
鸭子的副产品很多,鸭脖、鸭胗之外,还有咸鸭蛋。小时候各家各户都自己做,切开来,筷子戳下去,蛋黄冒油,方称隽品,如今会做的年轻人也不多了。

丁学良著《我读天下无字书》
丁学良著《我读天下无字书》,里面有个故事颇精彩,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时,与王小波、李银河夫妇相邻,来往频繁,发生不少趣事:“美国人也不喜欢吃鸭蛋,因为很腥。我们住所旁边的公园里有很多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我们捡回来,吃不完后,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这样味道并不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腌鸭蛋的经验:用牛拉的尿拌黄土来腌,吃起来会特别香。在匹兹堡这个钢铁之城,黄土不好找,牛尿就更不好找了。我后来又想了个办法——自己尿尿。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们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
食物及其味道,总是与我们的经历相牵连,分拆不开。何止鸭子是老的好,回忆也是愈老愈好。